說到母語,這又是令我迷惑的名詞。195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巴黎作出了如下定義:「母語是指一個人自幼習得的語言,通常是其思考與交流的自然工具。」在許多文化中,民眾從小在家或鄉里間習慣說的母語被認定是「方言」,在學校及正式場合則會以「標準話」來溝通。標準話與非標準話之間因此有著潛而不顯的地位高低。《那不勒斯故事》中出生在工薪家庭的女主角艾琳娜強調自己從小習慣說義大利語,讀者可看出那是她身為好學生的堅持,同時也能發現她對方言隱隱的鄙視。老城區的居民大多只有小學文憑,大字不識幾個通常只會說方言,但在小說中敘述所有人討論正經事、使自己有權威時都要說義大利語,只是教育程度不高的居民們總是艱難地說著不道地的語言。
「我們把科學爭論留給科學家,因為五個不同的人就有五種不同版本。我們創作音樂的方式從來不是用『我們有答案;這才是事實』的角度書寫,我們想打造一種氛圍,讓聽者感受它(在古代)的樣貌。」尤爾和瑪麗亞‧芙朗茲在維京歷史重演社團相識,並於2014年與維京紋身藝術家凱‧烏維‧福斯特共同組建了Heilung。從那時起,樂團就定下了「闡明歷史」的目標。先前發行的兩張錄音室專輯《Ofnir》和《Futha》復興了維京音樂、鐵器時代和青銅時代的文化,部分靈感源自芙朗茲收藏的大量文物與文本。
約翰‧馬魯夫從舊貨拍賣會上帶回一個裡面全是攝影膠卷的箱子,他只知道物品原有人的名字叫薇薇安‧邁爾,基於個人職業經驗與直覺,約翰開始逐一買回薇薇安‧邁爾被賣出的遺物,也因如此,約翰得到了更多薇薇安的膠卷、無數張她使用過的單據與信件、穿戴過的衣物與飾品、錄音帶與影片。這些細小繁瑣到令人幾乎產生密集恐懼的物品是薇薇安身體的骨,約翰因好奇開始追查並對薇薇安舊識的訪談則是她體內的血,而那數量龐大整理費時的攝影作品則是薇薇安的意志與靈魂,這一切融合成薇薇安‧邁爾這個人。當社會大眾多少次為薇薇安的作品發出震撼驚嘆,同時就有多少次為何這已是故人身後的惋惜,每個創作者都像薇薇安‧邁爾那樣矛盾、複雜、古怪並且遙遠嗎?《尋秘街拍客》這部記錄片裡有很大一部份的訪談都在描述薇薇安注重隱私而且極度孤僻的個性,每一個人的內心世界既不好懂也不易了解,但荒謬的是,有時人類居然又比任何一種生物更容易被看透被戳破,這莫不是身而為人的一種悲涼。





- 精神的毀滅、肉體的毀滅、信仰的毀滅、國家的毀滅,而我們依然繼續。
- 寫了七八年的影展簡介今年已經不想再寫了!就將!
- 既然考驗與羈絆難以避免,何不與它翩然共舞?
- 2022年,俄羅斯被禁賽的歐洲歌曲大賽,簡直超清爽!!
- 女性主義導論早就已經上完了,麻煩各位同學翻到第二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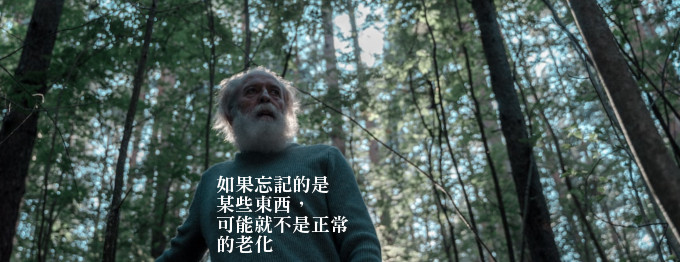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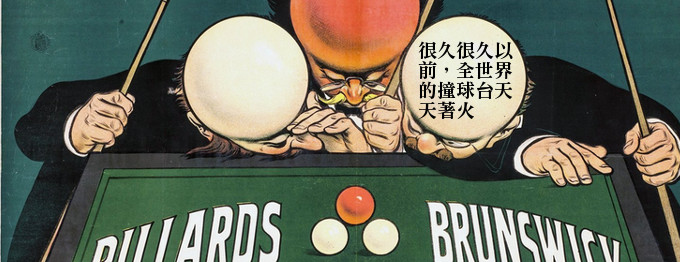




 最新文章
最新文章 主題總覽
主題總覽 成為粉絲
成為粉絲 在IG上追蹤
在IG上追蹤 RSS訂閱
RSS訂閱 合作提案
合作提案 贊助我們
贊助我們